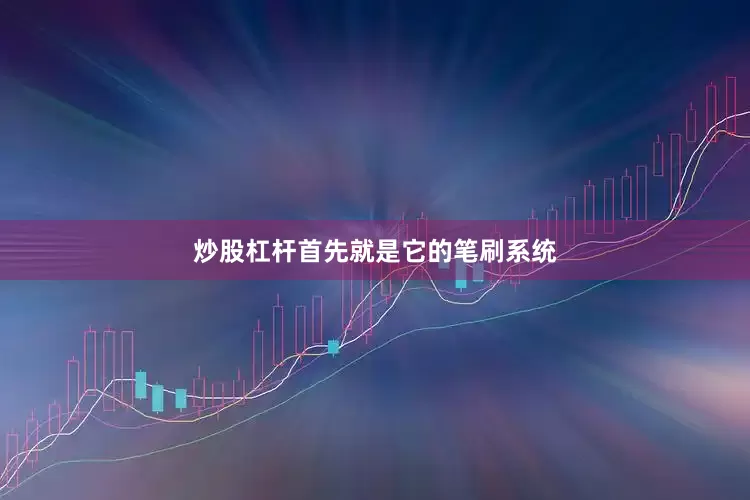日期:2025-07-20 08:20:12


▲陶铸、曾志夫妇
相识陶铸,重逢陶铸。
作者:曾志
《百战归来,我认此身:曾志回忆录》系我国铁血柔情的革命先烈曾志,于晚年病榻之上,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一部自传,亦是她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。书中,曾志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家世渊源,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,以及她的婚姻与家庭生活。她详细描绘了自己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胡耀邦等革命领导人的交往点滴,并亲身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。
曾志,原名曾昭学,出生于1911年4月4日,逝世于1998年6月21日,系湖南省宜章县人士。她的丈夫是陶铸,育有女儿陶斯亮。曾志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,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前副部长。
——编者
初见陶铸,印象不佳。
1930年10月的一个清晨,我作为厦门中心市委的秘书长,踏入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住所。在那里,我遇见了一位陌生的青年。他年约二十三四,身材并不高大,却显得异常精干。他那略显黝黑的面容,青涩的下巴,以及那头蓬松而坚韧的浓密头发,都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他那粗犷的眉毛下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坚定的光芒。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的广东风衬衫,搭配着西裤和皮鞋。虽然他谈不上魁梧英俊,也难以称得上潇洒儒雅,但那种逼人的英气却让人难以忽视。
罗明为我们相互作了介绍,我们彼此愣住了,一时间无言以对。啊,原来他就是陶铸!
此名号,我在闽西初闻时便已传为佳话。那震惊中外的“厦门劫狱”事件,总指挥一职便由一位热血华侨青年所担当,他更以此事为灵感创作了小说《小城春秋》,此作于195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,广为流传。那些从牢狱中死里逃生的同志们,之后纷纷投身于闽西苏区的革命事业。我通过他们的口述,得知陶铸同志不仅英勇无畏,而且才华横溢,因此,他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,且始终是那么正面而鲜明。

曾志
陶铸未曾料想,那在民间传颂的闽西苏区中,以泼辣干练著称的“母夜叉”,竟是一位肤色白皙、长发披肩的年轻女子,着装朴素得体,举止间透露出端庄大气,难怪他会感到惊讶不已。
然而,紧接着的瞬间,我对陶铸先前所留下的美好印象便荡然无存。
罗明与陶铸交谈之际,却发现陶铸正坐于椅上,目光投向窗外,似是漠不关心,对对话的态度显得冷淡。罗明因此显得有些恼火,质问道:“你能不能认真点?”陶铸则不卑不亢地回应:“难道我必须低头听你?”这番话让罗明一时语塞,气愤难平。
初次相见,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然而,随着我对他的深入了解和接触,我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。不久之后,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夫人那里,我得以见识到陶铸的另一面。
陶铸与王海萍,两位情谊深厚的挚友。1928年,广州起义不幸失利,陶铸遂赴上海,中央军委安排他投身红四军。在路经厦门之际,军委书记王海萍见其出自黄埔,且历经南昌、广州两次起义,深谙军事,实战经验丰富,遂诚恳地挽留,委以兵运及武装斗争之重任。初时,陶铸被派往厦门炮台担任兵士,历时三月,密谋兵变,意图夺取武器,继而又投身于劫狱行动。此劫狱之举成功,陶铸便在省委军委机关继续工作,与王海萍夫妇共居于机关之中。
曾有一段时间,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进行巡视与指导工作。然而,不幸的是,他的妻子恰在此时不幸患上急性腹膜炎。由于经济拮据,她未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便提前出院,在家中生活难以自理。王海萍将妻子托付给了陶铸照料,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前往闽西的路途。
陶铸全力以赴,倾注心血履行战友的托付,对王海萍病重的妻子关怀备至,体贴入微。他日以继夜地忙碌于内外事务,烹饪饭菜,喂药饮水,即便是倒尿倒屎、清洗污物等琐事,他也认真负责,毫无怨言。直至两个月后,王海萍终于归来。
我心生感动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里,我们这对原本扮演的假夫妻逐渐将戏份演成了现实,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

曾志与陶铸
陶铸被捕,涉嫌叛变。
1933年三月,上海中央局发布了一则通知,要求陶铸即刻赶往上海,并另行指派新的工作任务。在此过程中,省委书记的职位则将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替。
面对此次人事变动,陶铸虽感意外,却对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。直至一个月后,他在上海被捕并身陷囹圄,方才逐渐弄清了事件的真相。
原本,中央派遣至福州执行巡视任务的巡视员朱××,曾向陶铸探询其对王明的意见。陶铸性情直率,未加掩饰地吐露了自己的看法:“他不过是吃着洋面包,在我看来,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并不十分了解!”巡视员回到上海后,将陶铸的观点如实转告了时任中央负责人的王明。这却激怒了总书记,这次的调动,实则乃王明以莫须有的理由将其巧妙地撤职。
陶铸当时无从知晓王明的真实意图,然而,他心中已然明了,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关系。在此之前,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,实际上并未真正地共同度过一段和谐的时光。
在陶铸即将踏上征程之际,他在一家旅馆预订了一间客房。在那间房中,我们仿若一对恩爱夫妻,携手共度了十天的甜蜜“蜜月”。四月下旬的一个清晨,我们在旅馆的大门前,相互不舍地告别,珍重道别,心中满是不舍之情。
起初,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,信函虽简短,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。然而,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,消息突然中断,音信全无。
二十余日之后,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,特地前来告知我,中央传来消息,陶铸在上海被捕,已然背叛了革命。
冒险寄钱救陶铸
1934年三月下旬,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监狱的信件,信件由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。何家,便是我与外界沟通的联络点。信中,陶铸传达了这样的消息:他已被判处重刑,刑期之长,令人难以想象,他已无出狱的可能。他恳请我好好照顾母亲,并尽我所能去履行孝道。他还提到,自己在狱中身体欠佳,若有所回复,请将信件寄至南京军人监狱,编号为一二七一号。
在陶铸被拘禁之际,他曾秘密委托一位获释的难友,悄然传递出一张仅掌心大小的残破纸片,纸片上仅以寥寥数语,道出了“病重住院,生还无望”的悲凉心境。
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及叛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,但事实却使我卷入了其中,这让我时刻感受到一种沉重与苦闷。我对那些流言蜚语深信不疑,期盼着能听闻陶铸的真实情况。谁料,一年后,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亲笔信件。
我将信件递交给叶飞审阅,我们共同认同,鉴于判处无期徒刑,陶铸未曾叛变。我向叶飞提出,鉴于陶铸病情严重,是否可以汇些款项给他,他对此表示赞同。随后,我们从被没收的财物中取出20元,寄给了陶铸。
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,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。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,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,悬赏3000块大洋。但是不这样做,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。就决心去冒这个险!
我随交通员的引领,悄然潜入县城。据城内地下党人士所述,我离去不久,县城便骤然实施戒严,城门紧闭。警察与特务四处巡逻,严密搜查,声称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潜入城中。
数年后,陶铸在出狱后向我透露,他从福安寄出的款项和信件竟全部完好无损地抵达。彼时,他正饱受肺病折磨,咳血不止,我寄去的款项无疑如同雪中送炭。他用这些钱购买了鱼肝油,病情因此得以缓解。此外,他还购置了书籍,将牢狱视为学堂,勤奋读书数年,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,党中央将他成功营救出狱。因此,那次冒险的确是值得的!

▲陶铸、曾志夫妇
重逢陶铸于武汉
1937年9月,当我抵达武汉,自上海而来,已得知陶铸同志出狱后,正于湖北工委担任职务。甫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,我便立刻挥毫书写便条,告知陶铸同志我已安抵此地,并委托他人将此信件送往武昌。
约莫八点钟光景,陶铸急匆匆地赶到,一边喘息着,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,竟让我插不上半句话:“早些时候接到你的信,我欣喜若狂,迫切地想要立刻过江与你相见。无奈下午有个会议,我内心颇为焦躁,直至六点钟才赶到码头。恰逢大风肆虐,轮渡未能启航,我焦急万分。终于,在轮渡冒险开航后,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差点因此错过!”他话锋一转,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柔情,语气也变得柔和了许多:“对了,我还饿着肚子呢。不如我们去附近找家餐馆,边吃边聊吧!”
我面带微笑,静静地倾听着他的倾诉,内心既是甜蜜又是酸楚,情绪复杂纷繁。他消瘦得令人心疼,四年的牢狱生活让他面色苍白,两颊凹陷,眉目更显深邃,那件对襟盘扣的夹袄穿在他瘦弱的骨架上,摇曳不定。这样的他,哪里还像是一个28岁的青年,40岁似乎更符合他的外观。然而,从他的言谈间,从他那充满活力的眼神中,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热情洋溢、思维敏锐、如同烈火一般的陶铸。
“我出狱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了信,寄到了你母亲那里,等了二十多天音讯全无,焦急不已。没想到,转眼间你便出现在我面前,真像是梦中的景象。”忽又想起什么,他哈哈大笑:“当时我们正在开会,突然收到你的消息,我立刻心神不宁。钱瑛大姐还拿我开玩笑,说:‘曾志来了,瞧把陶铸高兴的,连汗毛都竖起来了!’”
“是上海党组织安排我前往延安的。”他诚挚地劝我说:“还是留下来吧,我会向郭述申同志(省工委书记)提出你的请求!”

陶铸与曽志
在夜深人静之际,陶铸提议道:“目前无法渡江,便暂且在此安顿一晚。”翌日破晓,他再度启程返回武昌。
第三日的清晨,我刚从睡梦中醒来,便迎来了郭述申的到来。根据组织的安排,我留在了武汉,并受省工委的指派,将担任省妇委的书记一职。
陶铸、李克农之“三岔口”。
我与陶铸在汉口寻觅了一处楼上的居所,厨房却设于楼下,系与他人共用。
夜深至凌晨两点,陶铸却未归家。约莫到了两点半,楼下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,我急忙下楼开门,只见陶铸沉默寡言,怒气冲冲地直上楼梯。我正欲上前询问,却惊见他额头鼓起一个如核桃般大的肿块。“难道是遭遇了特务的袭击?”我焦急地询问。他冷哼一声,愤愤回应:“我刚刚与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了争执!”
我惊愕不已:这岂不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?众所周知,李克农在营救陶铸及其同仁出狱的过程中贡献良多。陶铸获释后,曾前往办事处,意图与李克农面谈,以表感激之情,却不幸碰巧李克农外出,未能如愿相见。自此,两人便未曾相识。
当陶铸急匆匆地前往长江局寻找周恩来时,他的性情本就急躁,于是匆匆忙忙地跑上了楼梯。然而,就在楼梯口,一个身影突然闪现,他高声喝问:“何人?站住!”陶铸见对方如此凶狠,心中不禁有些不快,于是回敬道:“你这般官僚作风,喧哗些什么?”言辞间,对方已经一拳挥来。陶铸毫不畏惧,随手回敬一掌,将对方的眼睛眼镜击落在地,摔得粉碎。随即,两人便扭打在一起,从楼梯上一直打到楼下的客厅,依旧未曾罢休。
周恩来闻声迅速走出,声音严厉地喝问: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?”对方怒气冲冲地回应:“有人硬是要上楼!”周恩来定睛一看,认出:“那是陶铸!”随即他又指向对方:“他是李克农!”这样一来,两人方才停止了争执。尽管如此,他们仍心有不甘,一人指责道:“他上来时并未报明身份!”另一人则辩称:“是他先动的手,打伤了人!”
两位意气风发的资深干部,这一幕堪称精彩绝伦的好戏,在五十五年后,被《陶铸传》的作者幽默地比作“三岔口”。自此,每当陶铸与李克农重逢,提及此事,他们总会笑得合不拢嘴。
在武汉沦陷之后,我们再度面临别离。陶铸前往鄂中,而我则踏上了鄂西的土地。
1939年12月,我踏上了延安的土地。次年5月,陶铸亦自鄂中取道重庆,抵达了延安。随着抗战的胜利,我和陶铸一同奔赴东北,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陶铸、曾志、陶斯亮三人在1966年3月留下了珍贵的全家合影,这成为他们最后的共同影像。
在“文革”那段动荡岁月里,我家遭遇了不幸。1969年11月30日,陶铸先生在合肥不幸含冤离世。
旺润配资-股票配资知识网-股票如何杠杆-什么是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